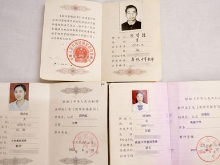那是1984年暑假,刚放假,我便被抽调参加湖南省高考阅卷工作。我们住在湖南财经学院(现在的湖南大学北院),那时,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都是自带床上用品,住学生宿舍。唯一不同于学生的,是我们4人一间房,每间房里装了一台吊扇,还有一个热水瓶。吃饭也是在学生食堂,洗澡在学生浴场。我因为当时在邵阳师专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任教,所以,高考阅卷自然分在了文科类语文阅评组,并被指定为第三小组组长。
阅卷报到的第一天,就是集中培训,讲评分规则,讲评卷纪律。那时也没什么通信工具,阅评组只有一台公用电话,24小时都有人监守,除非你有什么急事非得打电话,不然谁也不会去那里讨个没趣(守电话机的人像审犯人一样问这问那)。那时候,我们白天阅卷,晚上唯一的文娱活动就是统一在学校操坪里看电影。
语文阅评组的大组长是湘潭大学中文系主任、著名古典文学教授羊春秋先生,他学识渊博,治学严谨,为人宽厚,原则性强,令人敬慕。阅卷中,那些常识题、简答题、选择题和古文翻译题都好办,都有标准答案,两个老师相互一核对就行了。唯有作文是语文阅卷中的重中之重、难中之难。难就难在对标准的掌握上,多一分或少一分都有可能直接影响考生是否录取。所以,为尽量保证公平公正,阅评组先挑选出几篇作文,几位小组长讨论后,将它们分别列为“A”(80~90分)“B”(70~79分)“C”(60~69分)“D”(59分以下)4类的示范标准,供阅卷老师参考。此外,作文阅评,采取3人交叉阅评给分方式,即每篇作文要经过3个老师审阅,每个阅评老师把自己的阅评分填在记分空格里,然后,小组长综合大家的给分,一般在分歧不大的情况下,就直接给出具体分数(这就是考生作文的第一次具体分数),接着,再报语文大组审阅后就是确定分数(一般很少改变第一次的给分)。而对某些给分差异较大的作文,比如:甲老师给A,乙老师给C,丙老师给D这样的“差异卷”,小组长就很慎重了,把它们统一放在一块,再一起交大组组长,请他定夺。一般情况下,大组长与小组长协商一下就会给出具体分数,但也有争议较大的作文,这就要大组长召集全体小组长开会进行讨论。当年,就有七八篇作文提交全体讨论,其中有一篇作文争论最大,它是由我们小组提交的,这篇作文全部用文言文写作,我当时认为该文文字精练,很有文采,逻辑性强,观点独特,主张给90分。但有几个小组长强烈反对,认为中学不提倡用文言文写作,再则,这篇作文的观点有些偏颇,不符合中学生的逻辑思维。而另外也有几个小组长全力支持我的观点,认为高考就是选拔那些独特人才。双方为此争得面红耳赤,甚至拍桌打椅。就在大家争执难下时,羊春秋先生终于开口表态,他说自己仔细阅读了该文多遍,每读一次就赞叹不已,他认为该学生的古文功底堪称罕见,已达到报考古典文学研究生的水平,在词句上很难挑出毛病;其次,该文观点十分新颖独到,有创造性,不落俗套,作者是个难得的人才。因此,他一锤定音:90分!沉默些许后,全场掌声雷动,我当时头脑中很快闪过一个成语:伯乐相马。不是吗?!羊春秋先生和我们这些阅卷人就好像是“伯乐”,要在成千上万的高考学子中挑选一匹匹“千里马”。